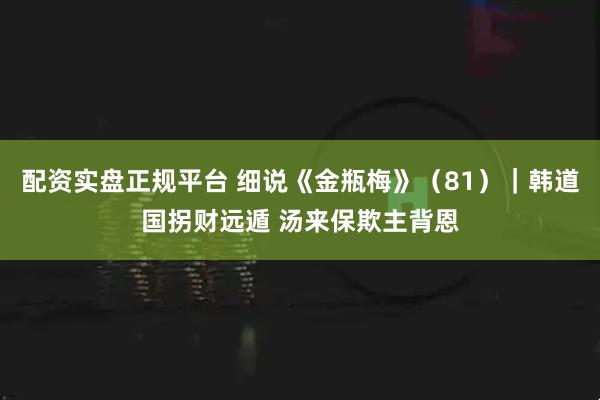
《金瓶梅》第八十一回,开篇诗曰:
燕入非傍舍,鸥归只故池。 断桥无复板,卧柳自生枝。 遂有山阳作,多惭鲍叔知。 素交零落尽,白首泪双垂。且说韩道国与来保领了西门庆四千两纹银,往江南采买货物。一路水程顺流而下,到了扬州地界,便寻着苗青的住处歇下。
那苗青念着西门庆昔日救他性命的恩情,待二人十分殷勤,不仅好吃好喝招待,还私下买了个名叫楚云的女子养在家中,打算日后送与西门庆,算作报答。
展开剩余93%可韩道国与来保却没把采买货物放在心上,日日流连勾栏瓦舍,要么找粉头陪酒,要么宿在娼家。
直到初冬时节,风里裹着寒意,岸边树木落得光秃秃的,一派萧瑟景象,两人心里才泛起几分归乡的念头,这才慢悠悠地拿着银子,去各处采买布匹,暂且存放在苗青家中,等着货物齐了再动身。
那段日子,韩道国常约着扬州旧院的王玉枝,来保则勾着林彩虹的妹子小红。
有一回,两人还请了扬州盐商王海峰和苗青同游宝应湖,玩了整整一天。
回来时恰逢王玉枝的鸨母做寿,韩道国又张罗着摆酒,还让随从胡秀去请客商汪东桥和钱晴川,可胡秀去了半天,人却没请来,倒是王海峰先到了。
眼看日头西斜,胡秀才醉醺醺地回来,韩道国借着酒劲骂道:“你这夯货,不知在哪儿灌了黄汤,到这时候才回来!嘴里的酒气熏得人头疼,客人都等了大半天,你倒好,全无半点分寸,明日再跟你算账!”
胡秀本就喝多了,被这么一骂,顿时来了火气,斜着眼瞪着韩道国,走到院子里就嚷嚷起来:“你凭什么骂我?你家娘子在家靠着旁人过活,你倒在这里寻欢作乐,把正事抛在脑后!府里老爷养着你家娘子,你得了便宜还卖乖,如今拿着老爷的银子快活,倒有脸说我?”
王玉枝的鸨母见他越骂越难听,赶紧拉着他往屋里劝:“胡官人,你醉了,快回房歇着吧,别在这儿闹了。”可胡秀偏不依,嗓门反而更大了。
韩道国在席上听见胡秀满口胡言,气得脸色发青,猛地站起身冲出去,对着胡秀踹了两脚,骂道:“你这狗奴才!我花五分银子雇你一天,还怕找不到旁人?现在就给我滚!”
胡秀却赖着不走,在院子里撒泼:“你凭什么赶我?我又没误了管账的事!你自己养粉头,倒来赶我,等我回了府里,看我不说给老爷听!”
来保见状,赶紧拉住韩道国,又把胡秀拽到一边,骂道:“你这没眼色的东西,喝了点酒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?”
胡秀还不服气:“保叔,您别管!我没喝多,今天非要跟他理论理论!”
来保懒得跟他纠缠,硬把他推回房里逼着睡下了。正是应了那句“酒不醉人人自醉,色不迷人人自迷”,两人的荒唐,早已把采买货物的差事抛到了九霄云外。
打发走胡秀,韩道国怕客商笑话,又强装笑脸回到席上,和来保一起陪着众人喝酒划拳。
王玉枝、林彩虹姐妹和小红三个粉头弹着曲儿、跳着舞,席间花团锦簇,猜枚行令,一直闹到三更天才散场。
第二天,韩道国还想找胡秀算账,胡秀却装傻说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苗青在一旁好说歹说,才把这事劝了下来。
又过了些日子,货物总算采买齐全,打包好装上船。
可苗青准备送给西门庆的楚云忽然病了,连下床都难。苗青只好说:“等她病好了,我再派人送过去。”随后备了些礼物,抄好账目,打发韩道国、来保和胡秀先动身。
王玉枝和林彩虹姐妹也在码头摆了酒,算是为三人饯行。
02一行人正月初十出发,一路上倒也没什么波折。直到船到了临清闸,韩道国正站在船头眺望,忽然看见街坊严四郎坐着船从上游过来,说是要去临清接官。
严四郎看见韩道国,抬手喊道:“韩西桥,你家老爷正月里就没了!”话音刚落,船就顺着水流走远了。
韩道国听了这话,心里咯噔一下,随即却暗喜,揣着这个消息,半点没跟来保提。
那时河南、山东一带正闹大旱,地里干裂得连草都长不出来,庄稼绝收,棉花布匹的价钱一下子涨了三成。各地的商贩都揣着银子,在临清码头等着抢货。
韩道国见状,就跟来保商量:“船上的布匹值四千多两,现在行情这么好,不如先卖一半。一来能少交点关税,二来剩下的带回家卖,也少不了多少。这么好的行情不抓,太可惜了。”
来保有些犹豫:“兄弟你说的是实话,可要是卖了货,回去老爷怪罪下来,咱们怎么担待?”
韩道国拍着胸脯说:“放心,真要是老爷怪罪,我一力承担!”来保拗不过他,只好答应。两人就在码头把一半布匹卖了,得了一千两银子。
韩道国又说:“双桥,你跟胡秀在船上等着交税,我带着小郎王汉,把这一千两银子先送回去,给老爷报个信。”
来保叮嘱道:“你到家后,记得跟老爷要封书信,交给钞关的钱老爷,说不定能少交些税,让船先过去。”
韩道国应了声,就和王汉把银子装成驮子,往清河县去了。
两人进城时,日头已经西沉。在瓮城南门,正好撞见看坟的张安推着车,车上装着酒米食盐,正要出南门。张安看见韩道国,连忙喊道:“韩大叔,您回来了!”
韩道国见张安穿着孝服,心里一沉,忙问缘由。张安叹了口气:“老爷正月里就没了,明日三月初九是断七的日子,大娘让我送这些东西去坟上,明天给老爷烧纸。”
韩道国心里咯噔一下,嘴上却应着:“真是可惜了,果然是路上行人说的那样,一点不假。”
他嘴上这么说,心里却打起了算盘:“要是现在去西门庆家,他已经死了,天色又晚,不如先回家跟老婆商量商量,明天再做打算。”
于是,韩道国带着王汉,牵着牲口,径直回了狮子街的家。两人卸了牲口,打发赶脚的人走了,叫开家门,王汉把行李和银子驮子搬进堂屋。王六儿连忙迎上来,帮韩道国脱了外衣,让他坐下,又让丫头倒了茶。
韩道国先把江南的事说了一遍,最后叹道:“我在路上撞见严四哥和张安,才知道老爷没了。好好的一个人,怎么说没就没了?”
王六儿撇了撇嘴:“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,谁能保证自己一辈子没事?”
韩道国说着,就把驮子拆开,将从江南带来的绸缎细软一一取出,又把那一千两银子拆成一封封的,都摆在炕上。王六儿凑过来一看,那银子白花花的,闪着亮,忙问道:“这银子是从哪儿来的?”
韩道国说:“我在路上听说老爷没了,就先把一半布匹卖了,得了这一千两银子带回来。”他又拿出两包私房银子,一共一百两,问道:“我走之后,家里多亏老爷照拂吗?”
王六儿翻了个白眼:“他活着的时候倒还罢了,现在他人都没了,你还打算把这银子送过去?”
韩道国迟疑道:“我正想跟你商量,咱们留些自用,把剩下的一半送过去,你看怎么样?”
王六儿冷笑一声:“呸,你这呆汉怎的还不清醒!这一回可不能再犯傻了!现在他已经死了,家里没人能管咱们,咱们跟他还有什么瓜葛?你要是把银子送过去一半,万一他们追问起来,反倒会查你的下落。不如一不做二不休,把这一千两银子带着,雇上牲口,逃去东京投奔咱们儿子。咱们亲家可是太师爷,还愁容不下咱们两口子?”
韩道国有些犹豫:“可这房子怎么办?一时半会儿也卖不出去。”
王六儿道:“你真是没主意!把你兄弟韩二叫来,留给他十几两银子,让他看着房子不就行了?等西门庆家的人来找你,就说东京的儿子把咱们叫走了。他们有天大的胆子,敢去太师府找咱们?就算真找去了,咱们也不怕!”
韩道国还有些良心不安:“可我受了大官人这么多好处,现在这么做,也太没天理了。”
王六儿哼了一声:“自古有天理的人,倒未必能吃饱饭!他占着我这么久,用他几两银子,算得了什么?前几天他孝期里,我还特意备了三牲祭品去他家烧纸,结果他那个大老婆,半天不出来,在屋里指桑骂槐,把我羞得无地自容。我想走又走不了,想坐又坐不住,后来还是他第三个老婆出来陪我,我没坐一会儿就坐轿子回来了。就冲这口气,我用他几两银子也不亏!”
王六儿一番话,说得韩道国哑口无言。夫妻俩当晚就商量定了。
第二天五更天,韩道国把兄弟韩二叫来,把事情跟他说了,又给了他二十两银子做盘缠。韩二本就是个好吃懒做的,一听有这好事,连忙答应:“哥嫂尽管走,这里有我呢,他们来了我来应付。”
韩道国随后把小郎王汉和两个丫头也带上,雇了二十辆马车,把箱笼细软都装上车,天刚亮就出了西门,往东京去了。
正是“撞碎玉笼飞彩凤,顿开金锁走蛟龙”,两人这一逃,算是彻底断了跟西门家的牵连。
03这边韩道国夫妇逃去东京不提,单说吴月娘。
第二天,她带着孝哥儿,还有孟玉楼、潘金莲、西门大姐、奶子如意儿和女婿陈敬济,一起去坟上给西门庆烧纸。张安趁机把昨天撞见韩道国的事说了。
吴月娘皱着眉:“他回来了?怎么不来家里?说不定今天会来。”
众人在坟上烧了纸,没坐多久就早早回去了。
吴月娘让陈敬济去韩道国家里看看,问问船到了哪里。
陈敬济去了之后,先是没人应门,过了一会儿韩二才出来,说:“我哥嫂被东京的侄女叫走了,船在哪儿我也不知道。”
陈敬济回去把这话告诉了吴月娘,吴月娘心里不踏实,又让陈敬济骑着牲口去河下找船。陈敬济找了一天,终于在临清码头找到了来保的船。
来保一见他,就问:“韩伙计不是先带了一千两银子回家了吗?怎么你来了?”
陈敬济急道:“谁看见他了?张安说看见他进城了,可昨天我们从坟上回来,大娘让我去他家,才知道他两口子带着银子逃去东京了!现在老爷已经断七了,大娘不放心,让我来寻船。”
来保听了,心里咯噔一下,暗自骂道:“这个天杀的,居然连我都瞒了!难怪路上非要卖那一千两银子,原来早就存了私心。真是人心隔肚皮,看着亲近,心里却藏着鬼。”
来保见西门庆已经死了,也动了歪心思,打算跟着韩道国学。
他把陈敬济这个毛头小子骗到码头的酒馆、歌楼里,又是喝酒又是找粉头,把他哄得晕头转向。暗地里,他却把船上八百两货物偷偷搬到客栈里,封好藏了起来。
过了几天,船交了关税,从钞关放了出来,到新河口卸了货,装上车往清河县运。回到家后,货物卸在东厢房里。
自从西门庆死了,狮子街的丝绵铺早就关了,对门的绸缎铺,甘伙计和崔本把银子交清后也辞了工,房子也卖了,只剩下门口的当铺和生药铺,由陈敬济和傅伙计看着。
没人知道,来保的妻子惠祥,有个五岁的儿子叫僧宝儿,而韩道国的老婆王六儿有个四岁的侄女,两人早就私下结了亲家,这事吴月娘一点都不知道。
来保把货物交了之后,一口咬定韩道国先卖了两千两银子带回家,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。
吴月娘几次让他去东京找韩道国要银子,来保却推脱道:“咱们可别去!太师府是什么地方?谁敢随便上门?平白惹祸上身可不值当。他不来找咱们,咱们就该念佛了,别没事找事。”
吴月娘还抱有希望:“翟亲家当初多亏咱们帮他保亲,说不定会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帮咱们。”
来保冷笑:“他女儿在太师府里正得宠,他只会护着自己的娘家人,哪会管咱们?这话也就跟您在家里说说,要是传出去,反倒让人笑话。依我看,这几两银子就当丢了,别再提了。”吴月娘听他这么说,也没了办法,只好作罢。
后来,吴月娘让来保帮忙卖布匹,来保找了买家来,吴月娘让陈敬济跟买家兑银子、讲价钱,可买家嫌价钱太高,拿着银子走了。
来保趁机说:“姐夫,你不懂做买卖的难处。我在江湖上跑了这么多年,知道行情。做买卖宁可卖了之后后悔,也别因为要价太高,把买家逼走。现在这行情,能卖到这个价钱就不错了。你把价抬得太高,买家走了,反倒显得你不会做生意。我不是说大话,你年纪轻,不懂这些。我还能胳膊肘往外拐,坑自家不成?不如赶紧卖了,省得夜长梦多。”
陈敬济本就年轻气盛,被来保这么一说,顿时来了脾气,说什么也不管了。
来保见状,立刻拿过算盘,把买家追了回来,当场兑了两千多两银子,一件件交给陈敬济,让他交给吴月娘。
吴月娘过意不去,给了来保二三十两银子做家用,来保却故意摆起架子,说:“大娘您收着吧,老爷没了,您一个人带着哥儿,日子也不容易,这点银子您自己留着用。我怎么能要您的钱呢?”
有一天晚上,来保在外边喝得醉醺醺的,闯进吴月娘的房里,趴在炕边,嬉皮笑脸地说:“大娘您这么年轻,老爷又没了,您一个人带着哥儿,不觉得孤单吗?”
吴月娘听了,气得一句话也没说。
又过了些日子,东京的翟管家寄了封信来,说知道西门庆死了,还听韩道国说西门家有四个弹唱的女子,让吴月娘报个价钱,他好兑银子来,把人接到东京伺候老太太。
吴月娘见了信,慌得手足无措,赶紧叫来保商量,到底是给还是不给。
来保进了房,连“大娘”都不叫了,直接说:“你一个妇道人家,懂什么?不给肯定要惹祸!这都是死去的老爷自己招的,以前摆酒请客,总把家里的乐伎叫出来表演,哪有不传出去的?何况韩伙计的女儿还在太师府里伺候老太太,她能不说?我前几天就跟你说过,现在果然出事了吧?你要是不给,他们随便派个府县的官来要人,你还能不给?到时候更难看。不如现在随便打发两个过去,还能留个体面。”
吴月娘犹豫了半天,孟玉楼房里的兰香、潘金莲房里的春梅,她都舍不得打发,绣春要照看孝哥儿,也走不开。最后只好问自己房里的玉箫和迎春,两人愿意去。
吴月娘就让来保雇了马车,带着玉箫和迎春去东京。
可谁也没想到,来保在路上竟然把这两个女子都玷污了。
到了东京后,来保见到了韩道国夫妇,把家里的事一五一十说了。
韩道国感激道:“要不是亲戚你在家拦着,我虽然不怕他们,也少不了一番麻烦。”
04翟谦见玉箫和迎春长得俊俏,一个会弹筝,一个会拉弦子,年纪都不到十八,很是满意,把她们送进府里伺候老太太,还赏了两锭元宝。
来保却私吞了一锭,回家只拿了一锭给吴月娘,还故意恐吓她:“要不是我去,这锭元宝都拿不回来!你还不知道,韩伙计两口子在东京过得多滋润,单独住着一所大宅子,使唤着丫鬟仆人,翟管家都管韩伙计叫‘老爹’。他们女儿韩爱姐,天天在老太太身边伺候,老太太对她百依百顺,要什么给什么,现在还会写字算账,越长越俊俏。前几天我见了她,打扮得跟仙女似的,一口一个‘保叔’,嘴甜得很。咱们家这两个乐伎去了,还得看她的脸色呢。”
吴月娘听了,反倒对来保感激不尽,摆了酒给他吃,又要给银子,来保还是不收,最后吴月娘给了他一匹绸缎,让惠祥做衣服,来保这才作罢。
后来,来保跟他妻弟刘仓去临清码头,把之前藏在客栈里的八百两货物全卖了,还偷偷买了一所房子,就在刘仓家旁边,开了家杂货铺。平日里,他要么跟亲友喝酒,要么去应酬,日子过得十分惬意。
惠祥则常常找借口回娘家,其实是去新房子里,换上金钗银镯、绸缎衣裳,去王六儿的娘家找王母猪攀亲家,还坐着轿子去看王母猪的女儿。
回到西门家后,她又换上粗布衣裳,装作一副老实本分的样子,只有吴月娘被蒙在鼓里。
有一回,来保喝多了,又跑到吴月娘房里调戏她,这样的事发生了好几次。
还有些丫鬟媳妇看不过去,跟吴月娘说惠祥在外边穿金戴银,还跟人攀亲家,潘金莲也跟吴月娘说了几次,可吴月娘就是不信。
惠祥听说后,在厨房里大吵大闹,骂那些传话的人。
来保则故意装出委屈的样子,跟人抱怨:“你们这些人,只会在家里说闲话!当初要不是我,家里这么多银子货物,早就被韩伙计拐去东京了,连个响都没有!现在倒好,你们不感激我,还说我吞了主子的银子,故意编排我的不是。真是好心没好报,自古信人挑唆,早晚要吃亏!”
惠祥也跟着骂:“那些嚼舌根的淫妇!说我们两口子吞了银子,在外边摆阔气。我回娘家,不过是跟我姐姐借了几件首饰衣裳,就被你们说成这样!你们是想把我们两口子赶走,好占我们的位置吧?就算我们走了,也饿不死!我倒要看看,你们这些人能在西门家待多久!”
吴月娘见他们夫妻俩又吵又闹,还动不动就寻死觅活,来保又三番五次在没人的时候对自己无礼,心里又气又急,却没什么办法,最后只好让他们夫妻俩搬了出去。
来保搬出去后,立刻跟他妻弟开了家布铺,卖各种细布,平日里依旧跟亲友喝酒应酬,日子过得十分自在。
正是应了那句“势败奴欺主,时衰鬼弄人”,西门庆一死,家里的奴才便没了约束,一个个露出了贪婪的本性,把西门家搅得鸡犬不宁。
(注:由于原著过于精彩,平台难以通过。笔者对本章几经删改隐藏配资实盘正规平台,已面目全非。若您想阅读原著无删减版内容,请私信我,回复“81”,免费赠阅本章内容。)
发布于:河南省嘉多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





